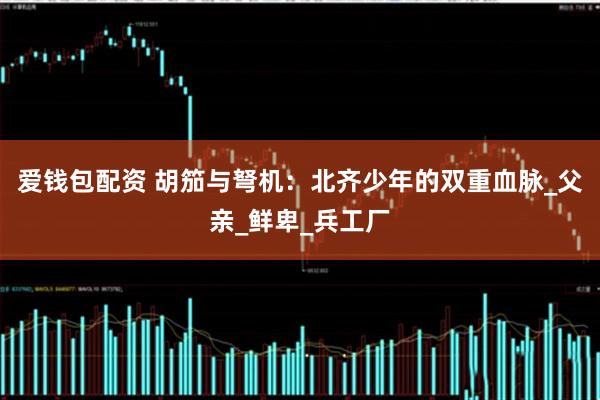
晋阳兵工厂的铁器味儿裹着煤烟扑面而来,斛律恒伽蹲在满地零件里,鼻尖快贴到那枚青铜弩机上。十二岁的少年手里攥着片磨得发亮的牛角放大镜,镜片把弩牙的纹路拉得老长,像极了他掌心纵横交错的茧子 —— 那是三年来拆了又装的鲜卑旧弩留下的印记,层层叠叠堆在还没长开的手掌上,看着比同龄人的脚后跟还要粗糙。
他的手指缠着半截灰扑扑的布条,是早上给高炉添煤时被火星烫破的,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捏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弩机卡榫。阳光从兵工厂的木窗棂斜切进来,刚好落在他发顶,把那簇倔强翘起的头发照得像团燃烧的火苗。墙上挂着父亲斛律光的明光铠,甲片在风里轻轻晃,护心镜里映出他紧抿的嘴唇和微微蹙起的眉头,活脱脱就是当年玉壁城下那个弯弓射敌的少年将军模样,连握东西时指节用力的弧度都分毫不差。
“又在跟这些铁疙瘩较劲?” 斛律光的笑声裹着甲胄的金属碰撞声飘进来,可当他弯腰看见儿子摊在地上的麻纸时,喉咙里的笑意突然卡住了。纸上用炭笔描着个怪模怪样的轮子,旁边标着密密麻麻的尺寸,“偏心轮连发装置” 七个字被少年描得格外用力,纸背都透出了墨痕。“这东西要是成了,顶得上十张鲜卑大弩。” 他伸手想去碰那图纸,指尖悬在半空又收了回来,像是怕碰坏了什么稀世珍宝。
恒伽猛地抬起头,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像淬了火的钢珠:“但偏心轮得用精铁铸,晋阳的高炉温度不够,练出来的铁脆得像冻住的河面……”
展开剩余78%“明日跟我进宫。” 斛律光的大手落在他肩上,掌心里的老茧蹭得恒伽脖子发痒,“你的本事,不该困在这煤烟里。”
那晚恒伽翻来覆去睡不着,摸黑溜进父亲的书房。月光从窗纸漏进来,刚好照在案头那卷《北齐律》上。“工匠不得入仕” 那行字被朱砂圈得像道血痕,旁边的批注力透纸背 ——“恒伽当破此例”,是父亲独有的苍劲笔迹。他悄悄摸了摸那行字,指尖沾了点没干透的朱砂,像沾了点滚烫的血。
转年春天,恒伽跟着父亲穿过晋阳的石板路。街上的胡商吆喝着卖胡饼,鲜卑武士的马靴踏得青石板咚咚响,他怀里揣着连夜画好的弩机图纸,布袋子被边角硌得发疼。进了宫城才发现,廊下的柱子上还留着去年鲜卑武士比武时砍出的刀痕,像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。
齐后主高纬捏着他的图纸笑个不停,金冠上的珠串晃得人眼晕:“十二岁的娃娃也懂军械?” 恒伽梗着脖子说:“弩机不认年龄,只认准头。” 这话让旁边的宠臣穆提婆嗤笑出声:“小工匠口气倒不小,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”
是父亲上前一步挡在他身前:“犬子虽幼,却能让弩箭快三成、准三成。” 说着解下腰间的鲜卑刀拍在案上,刀鞘上的榔头吞口在烛火下闪着冷光,“若陛下不信,可当场验看。”
那天的试射场设在宫墙下,恒伽改良的弩机射出的箭,整整齐齐钉在百步外的靶心,箭尾的白羽颤得像栖息的鸟。高纬看得直拍手,却在赏赐时只给了两匹绸缎:“赏你做件新衣裳,小孩子家玩这些就够了。” 恒伽望着父亲转身时绷紧的背影,忽然懂了为什么那些旧弩的弓弦总是绷得那么紧。
往后的日子,他总在兵工厂待到深夜。炉膛里的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,忽大忽小像个舞动的巨人。有次烧红的铁屑溅到胳膊上,他咬着牙没作声,直到父亲进来才发现他胳膊上起了水泡。斛律光用烈酒给他消毒,疼得恒伽直抽气,父亲却忽然说:“鲜卑人马上得天下,可马背载不动冶铁炉。” 他指了指墙角堆着的汉人手札,“你外祖父是汉人铁匠,我是鲜卑将军,你身上流着两样的血,这才是最好的砧子。”
十四岁那年,恒伽把偏心轮改成了更精巧的棘轮,连发弩终于成了形。他在零件内侧刻了两个鲜卑字 “必胜”,刻得太深,指尖被木刺扎出了血珠,滴在字上像给 “必胜” 点了红。父亲拿着成品在院子里试射,弩箭破空的声音惊飞了檐下的燕子,他忽然把恒伽拉到书房,从梁上取下个铁盒,里面竟是套完整的《考工记》手抄本。“当年打玉壁城,我从宇文泰的营帐里缴获的。” 他翻开其中一页,“汉人说‘智者创物,巧者述之’,你要做那个创物的人。”
可朝堂上的风总朝着相反的方向吹。有回穆提婆带人来兵工厂,拿起恒伽的弩机模型把玩,故意失手摔在地上:“什么破烂玩意儿,也配叫利器?” 碎片里滚出个小小的铜制齿轮,上面还留着恒伽用锉刀打磨的痕迹。是父亲及时赶到,捡起碎片说:“这齿轮能让十石弩变五石,省的力气能多杀三个敌人。” 穆提婆撇着嘴走了,留下满室的酒气,像打翻了的馊水。
恒伽蹲在地上捡碎片,父亲忽然按住他的手:“记住,好钢要经得住敲打。” 那天晚上,他在父亲的盔甲里发现个布包,里面是片风干的胡笳叶 —— 父亲年轻时在战场上吹过的。“当年我跟汉人将军学吹这个,他们说胡笳能解乡愁。” 父亲把胡笳叶放在他手里,“可真正的乡愁,是连自己人都容不下自己人。”
十八岁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,恒伽被任命为左卫将军的圣旨送到兵工厂时,他正蹲在雪地里调试新弩。传旨的太监尖着嗓子宣读完,旁边的老工匠们都红了眼 —— 谁都知道《北齐律》里那句 “工匠不得入仕”。他望着宫里的方向,忽然想起六年前父亲在《北齐律》上的批注,原来有些承诺,要用这么多年的风雪来浇灌。
就职那天,他穿着父亲亲手缝制的鲜卑袍,腰里挂着那枚刻着 “必胜” 的零件。站在朝堂的丹墀下,听着文武百官的议论声,有鲜卑贵族骂他 “匠人之子不配站在这里”,也有汉人官员说他 “忘了祖宗”。可当他抬头看见父亲站在武将列里,悄悄朝他竖了竖大拇指,忽然觉得那些声音都像兵工厂的风,刮过就散了。
那天退朝后,父子俩走在覆雪的宫道上。父亲忽然说:“明日带你去个地方。” 转天他们骑马出了晋阳北门,在片荒坡前停下,那里埋着父亲的老部下 —— 有鲜卑人,也有汉人,坟头的木牌都冻得开裂。“当年我们在这里打退过柔然人,” 斛律光蹲下来拂去牌上的雪,“他们的血混在一起,早就分不清谁是胡谁是汉。”
恒伽看着父亲的白发在风里飘动,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些改良的弩机,既要用鲜卑的牛角做弓,又要用汉人的桑木做臂。就像这天地间的雪,落在胡人的毡房上,也落在汉人的瓦檐上,本就没什么不同。
他回到兵工厂,把那片胡笳叶嵌进了弩机匣。风吹过的时候,偶尔会发出呜呜的声,像谁在低声哼唱。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,只知道炉膛里的火不能灭,手里的活不能停 —— 就像父亲说的,好铁匠从来不是看火候,而是看能不能把自己也当成块要烧的铁。 #自古英雄出少年#
发布于:湖南省配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